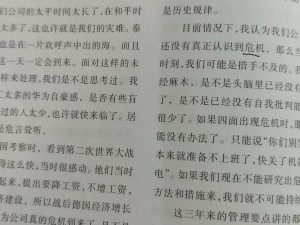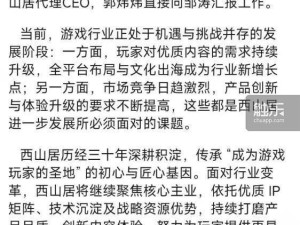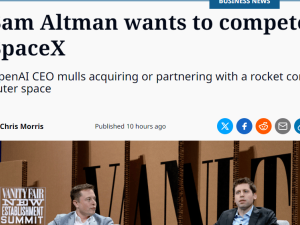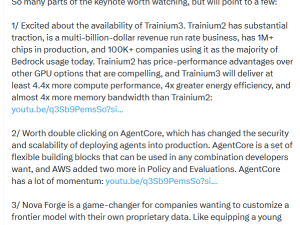在ICPC北京總部的一場座談會上,華為創(chuàng)始人任正非的發(fā)言引發(fā)了廣泛討論。面對青年學(xué)者與教練,這位79歲的科技領(lǐng)袖沒有重復(fù)“技術(shù)封鎖”的焦慮,反而提出一個顛覆認(rèn)知的觀點:“大量人才赴美發(fā)展是件好事。”這一論斷如同一顆石子投入輿論湖面,激起層層漣漪——有人質(zhì)疑其立場,有人擔(dān)憂人才流失,但更多人開始重新思考: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,人才流動的本質(zhì)究竟是什么?
任正非的“反常”言論,實則指向一個被焦慮掩蓋的真相:科技競爭的核心從來不是“圈養(yǎng)”人才,而是構(gòu)建開放的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。他以華為自身經(jīng)歷為例:早期研發(fā)團隊中,許多成員擁有海外學(xué)術(shù)或產(chǎn)業(yè)背景,他們帶回的不僅是技術(shù)知識,更是跨文化的管理經(jīng)驗與研發(fā)思維。這種“全球育苗、本土開花”的模式,讓華為在通信領(lǐng)域?qū)崿F(xiàn)了從追趕到引領(lǐng)的跨越。“技術(shù)無國界,關(guān)鍵在于吸收與轉(zhuǎn)化能力。”任正非的潛臺詞清晰可見:若因恐懼流失而封閉國門,無異于主動放棄接觸前沿的機會,最終矮化人才的成長空間。
這種開放思維同樣體現(xiàn)在華為對技術(shù)封鎖的應(yīng)對上。被制裁四年間,華為研發(fā)投入不降反增,其秘訣在于“在限制中尋找開放”:通過參與開源社區(qū)、國際標(biāo)準(zhǔn)制定、跨企業(yè)技術(shù)聯(lián)盟等方式,持續(xù)融入全球科技網(wǎng)絡(luò)。任正非將此比喻為“戴著鐐銬跳舞”,強調(diào)封閉只會走向自困,而開放才是突破困境的必由之路。他以美國半導(dǎo)體產(chǎn)業(yè)為例:其強大源于整合全球材料、設(shè)計與制造資源,而非孤立發(fā)展。這種“消化再創(chuàng)新”的邏輯,正是中國科技從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的關(guān)鍵。
在AI領(lǐng)域,華為的選擇同樣體現(xiàn)務(wù)實主義。當(dāng)行業(yè)熱衷于追逐“通用人工智能”的宏大敘事時,任正非將目光投向工農(nóng)業(yè)場景:“未來3-5年,大模型應(yīng)優(yōu)先解決產(chǎn)業(yè)痛點。”這一判斷源于對中國制造現(xiàn)狀的深刻洞察:大量工廠仍依賴經(jīng)驗驅(qū)動,質(zhì)檢依賴人工目檢,而AI技術(shù)恰好能將這些隱性知識轉(zhuǎn)化為顯性算法,推動中小微企業(yè)數(shù)字化升級。這種“技術(shù)賦能”的思維,比單純爭奪“AI第一”更具長遠(yuǎn)價值——科技的使命是讓復(fù)雜技術(shù)變得可用,而非讓簡單問題復(fù)雜化。
任正非的發(fā)言中,另一個值得關(guān)注的觀點是對教育與企業(yè)邊界的厘清。他直言:“教育培養(yǎng)人,企業(yè)用好人,兩者目的不同,應(yīng)避免混淆。”現(xiàn)實中,高校為追求“產(chǎn)學(xué)研結(jié)合”過度側(cè)重應(yīng)用研究,企業(yè)為儲備人才要求大學(xué)開設(shè)定制課程,這種“責(zé)任錯位”導(dǎo)致基礎(chǔ)學(xué)科萎縮與人才培養(yǎng)斷層。華為的“天才少年”計劃則提供了另一種范式:不要求高校輸出“成品人才”,而是通過企業(yè)實戰(zhàn)項目加速青年成長。這種分工模式——教育提供“毛坯”,企業(yè)負(fù)責(zé)“精加工”——或許比籠統(tǒng)的“校企合作”更能釋放人才潛力。
從人才流動到技術(shù)開放,從AI落地到教育分工,任正非的論述貫穿著一條主線:真正的科技自信,源于對世界多元性的承認(rèn)。他提醒,科技競爭不應(yīng)被簡化為零和博弈,人才的價值在于創(chuàng)造而非歸屬,開放不是妥協(xié)而是生存本能。當(dāng)行業(yè)沉迷于“卡脖子”的焦慮時,華為選擇在開放中突破;當(dāng)輿論糾結(jié)于人才流失時,任正非看到的是知識溢出的長期回報。這種穿透表象的理性,或許正是中國科技穿越周期、實現(xiàn)躍遷最需要的定力。